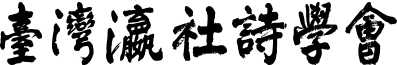明末清初經世文論研究
出版社: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出版地:臺北市
本會會員學術論文(博士論文)
序及提要並錄
序
處理完最後一頁列印資料,心中並沒有預期中的如釋重負之感。這是最後一次以學生的身分提出類似讀書報告的作業,呈請師長指正了。在臺大,十五年于茲,多得是這種機會,而今煙雲將逝,才開始遺憾過去的虛擲,想來自不免有幾分惆悵。這篇論文就用來「以誌吾愧」罷!
但是,如果說這篇論文只有「誌愧」的意義,那不僅是妄自匪薄,而且更非實情。因為我已經盡力去完成了;雖然很難說有什麼成果,畢竟也代表了一點點的收穫。最重要的是,如果沒有吳宏一老師的指導和鼓勵(有時候,「令人知愧」倒是很有效的鼓勵方式),這篇論文可能更加不忍卒睹;沒有楊儒賓的閱正,前三章的破綻,可能更無法瀰縫;蔣秋華是最忠實的讀者,大則一章一節,小則一字一句,都使我深深感受到「益友」的意義。至於在編排校對上,更是傾力協助,沒有他,這篇論文恐怕只是一堆爛紙而已!我豈能因為一己之愧,就抹煞了他們對這篇論文的貢獻?「得道者多助」本來是值得慶幸的,可惜的是自己愧於「道」者良多,又錯失了太「多進于道」的時機;祇願日後進德修業,這些良師益友不會由於吾愧而棄之。是為序。
提要
自宋儒提出「文以載道的觀點以來,所謂的「載道」理論,一直在中國文學批評史,中尤其是文論部分,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雖然批評家可能以各種轉換、迴避的方式,巧妙地因應個人論點所需,賦予「道」不同的內涵,而作新的註釋;但是在面對這四個字的時候,幾乎都一致地採取肯定的擁護態度。即使是刻意強調個人情思的批評家,如公安、竟陵諸人,甚至一向被目為離經叛道的李贄、金聖嘆等,在倡論了個人情志的真摯浪漫、自由奔放之後,也不得不或隱或顯地「矯訛翻淺,還宗經誥」。在傳統「重儒宗經」的格局中,其所詮釋的「道」,自無法逸離儒家思想的範疇,這是可以想見的;也正因其所謂「道」受限於儒家思想中,所以「文以載道」有時也成為學者刊落「一切異端邪說」,或不符合當代學者倫理觀念的作品及利器,佛老諸子之文、詞曲小說之作,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中,往往無法受到應有的肯定與確切的評價,也正肇因於此。於是,「文以載道」之說不但成為儒家獨霸的名言,更成為迂腐、固陋、封建的象徵,近代的文學批評家,鮮有不施加嚴厲的批評的明末清初經世文論研究,更遑論深入探討,指出其說的真下意義了。
基本上,「文以載道」是一種「文學功用論」,強調文學必須肩負起道德、教化的責任,這是文學存在的唯一價值。狹隘地解釋的話,文學只不過是「道」的附庸而已,唯有依附於「道」,文學的存在才有意義可言;是則,其淪為政令宣導、思想禁制的可能性,顯然是很難避免的。不過,眼光廣闊些,考慮各個時代的思想潮流必無可避免地會呈露、表現於文學之中的因素,則文學於此一「道」,未必即只是附庸的工具,而是可以與之相提並論、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的了。何況,「文以載道」既強調教化的功能,亦無異承認文學的相互感通性,因此,如何加深其相互感通的力量,以達成教化目的,便不能不於「道」之外,求諸於文學自身。如此一來,只要原則上不違於「道」,文學未必不能反賓為主,相應於不同的時代作長足的發展。即此而言,「文以載道」之說,實際上未必會阻礙文學的發展,中國文學自宋代以後的輝煌成就,應是絕佳的證明。而「文以載道」之說的發展,事實上也是從宋代以後,由狹趨廣,逐步擴大、完成其理論系統的。
「文以載道」的淵源,當然可以遠溯至孔子「思無邪」、「興觀群怨」、「不學詩無以言」等名言,然而,卻要到宋儒,如周、二程、朱子,才正式揭櫫了這個宣言。在此之前,尚有蕭綱敢於倡言「立身先須謹重,文章且須放蕩」,在南北朝之際帶動了唯美文學的發展;但是自宋儒以後,這種將道德與文學截然區劃為二的觀念,就鮮少出現,更遑論形成一股潮流了。宋儒切切以「聖學」為念,上承唐代韓愈提出的「道統」之說,結合著當時的「理學」,將文學限制在一個相當狹隘的框架中,以為「文是自道中流出的」,沒有「道」,文即不可能獨立存在,文學只是「道」的附屬品,學者所務,唯在「明道」,一旦鑽研於文學,就是「翫物喪志」。無形之中,文學的價值就被否定了。宋儒雖自詡其所謂的「道」,為孔、孟一脈相傳的真理,但實際上是否符合孔、孟之意,恐怕不無疑義。至少,孔子就不曾否定過「文」,「郁郁乎文哉,吾從周」、「文學:子游、子夏」之語,反而都是對文學的一種肯定。宋儒以「文以載道」作為宣言,將文學視為末務,不但抹煞了孔、孟對立言的重視,以及「興觀群怨」的社會功效,更顯與「周孔作制」的精神背道而馳(畢竟,「作制」之意,正是企圖通過「文」而達成教化的目的),這種偏狹的觀念,即使純粹以儒家思想的尺度加以衡量,也是有所不足的。